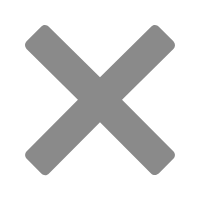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
纱帐之恨
1
哥哥是村里出了名的无赖,在村里人憎狗恶。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他却在中元节那天带回来一个长相极为妖艳的女子。
村里好心的林阿婆劝他将人放回去,他却反将人打了一顿。
他见识浅薄,不知中元节带回的除了妻子是满身怨念的厉鬼妻。
我知道,可我私心不愿告诉他。
中元节的第三日,哥哥便迫不及待将嫂子迎进门。
娘咬了咬牙办了两桌酒席,可嫂子宽大的裙摆之下,分明只有一双红绣鞋在动。
1.
我扶着美艳的嫂子进了矮小破旧的婚房,盯着她的红绣鞋看了良久。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嫂子并像不在走路,反倒是像…风筝般飘着。
“大妮,你哥哥他以前娶过妻子么?”空灵的声音似鸭羽般轻轻落在我耳边,如平静湖面上激起的巨大浪花。
我的思绪渐渐被拉扯,想到了曾经那位既可悲又可怜的女子。
她是哥哥第一位妻子,听娘说是她花了大价钱从城里买回来的“大学生”,可有文化哩。
那时娘还打包票说那个大学生肯定会给她也生个大学生孙子,光耀门楣。
她同我们不一样,浑身散发着光芒,眼里从不缺那名为自信的东西。
她说我这样聪明善良不该拘泥于山村,她说等她爸爸来接她,她会央求爸爸带我一起离开这儿。
禁锢又封闭的内心仿佛裂开一道口子,我拼命顺着光往外爬,却因一步之遥被永远困在这儿。
我曾在夜里悄悄给过她半块馍馍,也曾在雨天给她送过避雨的芭蕉叶。
作为回报,她教我习字读书,可她死在了宗堂,死在猪圈里。
“大妮?”清脆带着疑惑的嗓音拽回了我的思绪。
“姐姐,你是自愿嫁给我哥的么?你了解我哥么?你知道…”
我想不明白她长的那样美,为何独独选了个如此丑陋粗鄙的男人。
哥哥阴沉着脸自身后大步而来,抬手一巴掌打的我摔在地上,右脸火辣辣的疼,以惊人的速度红肿起来。
我哥扬起手还要打,却被嫂子温言软语伸手拦住,嘴里却还不断辱骂着肮脏下流的话。
“李大妮老子是不是太惯着你了?是不是皮痒了欠揍?皮痒了就去宗堂睡着!”他啐了口浓痰吐在我边上,又伸脚狠狠踹向我的腹部。
我疼得抱着肚子,泪水滴溅在满是灰尘的院子里,瞬间消失殆尽。
起身时二人已离去多时,破旧的木门里迫不及待的传来阵阵女子娇吟声和男子野猪般的粗喘。
宗堂…那是我一生的噩梦。
拖着疼痛的身子回到自己的柴房,瑟缩在积灰的角落,缓缓伸手一笔一划写下了熟记于心的名字。
“楚念冉,是你回来了么…”
没人回应我的呢喃,墙缝钻进来的那缕风给了我答案。
我抱着膝盖掩下嘴角那抹淡淡的笑意,往事如昨日,浮现在我眼前。
楚念冉被拐来的时候怎么打都不听话,她说她爸爸是是英雄,迟早会找到她的。
为了磨去她的铮铮傲骨,日日毒打挨饿,只用一碗脏污的河水吊着命,村里男人日日轮番侮辱,慢慢摧毁掉她眼中全部的信念。
是的,在我们村,不听话的女人会被扣上沉重的铁链,栓住脖子与脚,如同母狗一样毫无尊严的被栓在猪圈。
而调教女人的方式,则是全村男人齐上阵。
我曾见过不下十次这样的场面,他们待女人如猪狗,死在他们身下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年年复年年,年年有今朝。
猪圈里撕心裂肺的哀嚎声足足响了一下午,在后山柳树林里割猪草的我仿佛都能听见那群男人的狞笑。
到了夜间依旧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滴水未进的她再发不出一点声音。
这样残忍的折磨方式会一直持续到她心甘情愿呆在这儿,甘愿在这生下儿子为止。
可我从未见过有几个像她这种城里人能甘愿在此堕落的。
我有时偷偷攒下半块干硬的馍馍,趁着半夜三更猪圈无人时给她送去。
她浑身青紫,不着寸缕的抱着馍馍无意识的啃咬,眼眶通红却还是忍不住朝我求救。
我心软了,趁着夜深去娘屋里偷了钥匙给她开锁,却在逃跑的路上被全村人带着火把在柳树林里抓了现行。
只差一步,她便能逃离这“吃人”的鬼地方。
“姐姐…你不属于这…你走吧…”我话未说完,却没想到她一手狠狠掐着我的脖子,掐的我脸涨的通红。
“都给我滚啊,再过来我杀了她!”她的指甲很长,白日里因为挣扎,划伤了王屠户,竟生生被他拔下。
“好啊,我说我家大妮怎么会帮外村人,合着是你这个贱皮子…”我娘尖锐的声音鼓动着人心,她毫不在乎我的生死,冲上来就要打她。
我深知娘并非替我开罪,而是我这条贱命有副好颜色,再养几年便可以卖给别人,得一笔高价彩礼。
逃跑以失败告终,我被娘拽着头发连着打了几个巴掌,整个头肿胀起来,口腔中浓郁腥甜。
这还不算完,只是开胃小菜。
忌惮我毁容,她落不到彩礼。
她把我拖回院子用极细的柳条狠狠的抽我的皮肉,觉得不够解气便沾着盐水继续抽,柳条上沁满了我鲜红的血液。
浑身无一块好肉,把我扔进了柴房,一碗水,一个脏馍馍。
她要惨的多,当场被打断两条腿,以怪异的姿势扭曲着被一路拖了回去。
一路蜿蜒的血痕和碎肉,那是我一辈子不敢回忆的噩梦。
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反抗的机会,却以失败告终。
这场逃亡引起了村民的公愤,说她不守“女德妇道”,那夜宗堂传出的惨厉叫声以致我现在闭上眼还能听见。
她断了一双腿,我哥却心怀恨意,于是她便成了我哥的挣钱工具。
只要十块钱,就能和她春风一度。
不能否认她的脸长的极美。
所以每日进进出出猪棚的人不减反增,他们自诩正义,说要狠狠“惩罚”赶跑的女人,却在大祸来临时,一个个愚蠢如猪。
我日日出去打猪草都能听见婶子们毫无休止的谩骂,连带着看我的眼神也愈发厌恶起来。
男人管不住自己,却要怪那个可怜人。
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我睡的不太踏实。
照例煮了稀饭蒸了馍馍,拿上院里堆砌的脏衣服便要去河边。
开门却遇上刚从外面回来的嫂子,她周身萦绕着一股水汽,像是刚沐浴完,手上捏着一把细细的柳条把玩。
我盯着柳条看了一瞬,移开目光,是我的错觉么?她怎么…比昨日更美了。
“起这么早啊?”
她笑着跟我打招呼,我虽心下惊疑她长的像那位,却也没说什么,只道锅里有饭让她记得吃。
她笑着应下,施施然回了房间。
晨间雾气浓重,行动间露出裙摆下纤细的脚腕。
那脚腕细的仿佛透明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