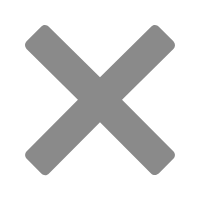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
不堪折
1
我是妖。
一朝化型,我便迫不及待选秀入宫……
因为花婆婆说,英雄救美本为佳话,可报恩也要分情况,若那英雄长得俊,便“以身相许”,若是长得丑,便“来世做牛做马”,
后来,世事无常,我躺在冷宫外乱葬岗的血水泥浆里,碰到一个捡尸的皇子。
1
李恕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我封为贵妃。
朝堂之上一片哗然,群臣又是上疏又是死谏,李恕不管,砍了几个人的脑袋,然后将我拖上龙床。
“姐姐……”
他覆身压上来,吻住我的唇。
“大逆不道!”我挣扎着避开:“按理你还得叫我一声‘母妃’才是!”
“母妃。”
他从善如流,果真叫了一声。眼中尽是颤栗的兴奋和压抑的疯狂。
我心肝儿俱是一抖,对着他那张脸便是一踹。
“砰”地一声。
不知是磕到了哪里,李恕再抬头时,额角破了个窟窿。
他淌着满脸的血,毫不在意地低笑一声,抬手捞住了仓惶逃窜的我。
掌心扣住我的脚踝,竟意外地灼热。
他跪伏在塌上,流连轻抚过我的小腿,低头轻嗅,神色痴迷,喊:“仙人……”
我一时忘了挣扎。
火光电石间,我忽然反应过来什么,又不可置信,问他:“你是不是吃了寒食散?”
李恕没有说话,但他的反应已经证实了我的问题。
“荒唐!”
我气急之下,竟扇了他一巴掌。
“谢予白!朕现在是皇帝!”李恕微恼,按住我,掐着我的脖子,扯开我衣襟:“朕想杀你,轻而易举。”
衣衫尽落。
李恕动作粗暴,指腹和掌心的茧子磨得我身上生疼。
喘气不及,呼吸都艰难,我感觉我要晕过去了。
昏昏沉沉,耳边是李恕混乱模糊的呢喃。
“乖乖听话……”
“好歹是第二次做贵妃,侍奉得了李兰泽,侍奉不了我吗?”
“你不也情动了吗?”
“……”
我暗暗咬牙:混账东西!
丹田仿佛填满滚烫岩浆,最后一步我险些受不住。
我还没喊,李恕那小子倒抱着我先哭起来了:“对不起……”
我知他是发了散,松下一口气,又听得他哽咽:“谢予白……‘寒食散’有毒是吗?我喝了会死,对吗?可是,不喝也会死。”
“救我。”
他说。
“仙人,仙人……”
他反复念着,将我拉进更深的漩涡。
2
从八岁到十八岁,我陪了李恕十年,直到他生辰那日,被接回去继位——
“咚、咚、咚……”
四十五声钟鸣,皇帝驾崩。
李兰泽死了。
我清楚地感受到丹田的异样。
李恕问:“怎么了?”
我勉强牵起一抹笑,说:“你的气运要来了。从前我不是说过嘛,你是将来要做皇帝的。诓了你这么多年,总算能兑现了。”
李兰泽不可能有其他子嗣,我知道。
当初,李兰泽以为是我用毒害得茗美人小产,却不知,那半步莲,虽下在茗美人身上,却是给他用的。
李兰泽日日与她交欢,实际是在断自己的子孙啊。
唉,只是没想到李兰泽早年在冷宫还留了一个种。
除了李恕,皇室再无血脉。
我交代他,不必管我,出去之后只管听安排,哪怕是做个傀儡,他也能高坐在那龙椅上,锦衣玉食,一世无忧。
太后携皇后与各宗亲大臣亲临,宣了懿旨:“……应天顺时,受兹明命……皇长子李恕……择日登基……”
随行的内侍宫女口称“陛下”,乌泱泱跪了一片。
李恕被他们带走,临走前慌乱回头。
我知道他是在寻我的身影,可我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安抚那个少年了。
我闪身躲进窗内,避开他仓惶的目光,然后靠着墙缓缓蹲下,长出一口气,怅然若失,又如释重负。
丹田处一阵空虚,又夹杂着丝丝缕缕细微的疼。
李兰泽死了。
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是爱?还是恨?亦或是又爱又恨?
初承宠时,我也是风光无两,他柔情蜜意,与我说白头偕老,同衾共穴,后来,他有了新人,便冷了,淡了,将我一脚踹了。
当朝尚服“寒食散”,那玩意儿有毒,为救李兰泽,我剖了半颗金丹,最后换来他一句——“杖毙”。
罢了,左右还他一命了,现在将李恕那小子送出冷宫,我便在这破院了此残生吧。
然而没等我闭眼,就被一道圣旨召回,还被封贵妃,赐未央宫。
李恕那小子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不顾纲常人伦,睡了他小娘!
可笑的是,我不仅反抗不得,还得救他。
我是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要被这父子俩相继磋磨?
我是欠了李兰泽的恩情,可我就这么一颗金丹,赔给了他半颗,还要再给他儿子半颗吗?
3
“喊再多‘仙人’都没用,”我双眼空洞地望着头顶明黄的帐子,声音缥缈:“我救不了你,我救不了……”
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如何再渡一人?
……
“李恕,”我捧着他的脸,轻声与他商量:“把‘寒食散’戒了好不好?”
他吻着我眼角的泪迹,说:“戒不了,不能戒。”
因为那是太后赐的。
每日一剂,雷打不动,由宫人端过来,那宫女内侍非得看着他喝下去才肯离开。
我看着李恕笑着,接过玉碗,仰头一饮而尽。
寒食散这东西,不仅蚕食人的身体,还会腐蚀人的心智。
李恕的瘾越来越深了,也越来越像疯子了。
他唆使、纵容臣下将亲眷带进宫中一起享用“神药”,然后一起“发散”。
男男女女,殿中脱衣褪帽、袒胸露腹,披头散发,放浪形骸。
癫狂又荒诞。
李恕飘飘然看着他们聚众淫乱,然后大笑着寻我要“清凉”。
红烛泪烧,帐中人影晃动。
李恕双唇滚烫,犬齿叼着我颈间软肉细细碾磨,含糊道:“仙人……”
听到这两个字,我心下又是一阵烦躁。
一只手被软绸缚着,我从满身黏腻中抽出另一只手,搡他:“别叫我‘仙人’,‘仙’什么‘人’?!”
他改口,胡乱喊,喊“谢予白”,喊“姐姐”,喊“母妃”,攥着我的脚踝,用力到像是要搓下我一层皮肉。
我脚踝上有颗小痣。
也不知李恕什么癖好,做的时候总爱揉搓那块皮肉,用力时更是又扣又掐,非得看着那白腻上浮起一片绯红才肯罢休。
我“嘶”地一声,泄愤般咬在他肩上,直到尝出血腥味,才松口,骂道:“疯子!晦气!你娘早死了!想喊去她坟上喊。”
折腾了半夜,入睡时却忽然听得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没坟。”
李恕散了热,懒下来,意识也有些模糊了,抱着我说:“我吃了她的肉,骨头喂了乱葬岗的野狗。”
反应过来,我只觉遍体生寒。
疯子。
心中涌起一阵恐惧,而后又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