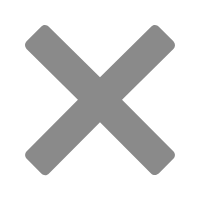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
震惊!我和堂哥结了阴婚!
1
为了大伯娘口中六位数的嫁妆。
我连夜收拾行李赶回老家去相亲。
然而,我没想到,这竟然是场阴婚!
更搞笑的是,我还是小三!
而我的阴婚对象竟是……
1.
“林依?林依!”
“哎!”我猛地抬头,抬眼看到喊自己的,是在阳台处站着的舍友。她手里提着还在滴水的床单,下颚示意地抬了抬。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是想要我过去帮忙拧床单的水。我连忙放下手里的剪刀,快步跑了过去。
舍友语气埋怨:“你怎么回事啊!喊了让你那么多声都不应我,这个床单重死了。”
我不好意思地冲着她笑了笑,手上拧水动作不停,语气迟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刚就好像有人在拉扯着我,让我去一个地方。”
“宿舍就我和你在,刚刚我离你几步远呢,哪有什么人拉着你,别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中了邪吧。”室友不满地絮叨。
我听着这些话不太舒服,张了张口想要辩解,但我不能说。在这个宿舍里,只要我的意见和她们不一样,我后面行为动作会被她们直接忽视,那样我会过得很难受,我只能埋头将手上布料的水分弄干。
刚弄完准备晾起来时,室内桌上的手机嗡嗡地响了起来,接着开始大喇叭放着歌,是我的手机。
室友不耐烦了,冷笑一声,一手将床单扯过,直接大力拍了我一巴掌:“赶紧去接电话,你这手机铃声听得我不舒服。”
被拍到肩膀的地方,火辣辣的疼,我不敢多说话,只好把东西放下,几个大跨步快速地走进寝室,抄起响个不停的手机看,是个没有备注的电话。正迟疑着,余光看到了室友冰冷的眼神,手一抖,划拉到接听键:
“喂?”
“林依啊,是林依吧?”
“哎大伯娘,是我,你怎么用这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了?”
“我那手机摔啦,还没买新的,依依呀,你这次清明放假吧?”
“放的,怎么了?”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邻村李婶家有个儿子,想要和你见见面聊聊天。你不知道吧,他家可有钱了,那别墅高得哟,六七层,今年还买了车子。最重要的是,你家最近不是缺钱嘛,他家说了,要是看你满意,能出到六位数!你这次就趁着放假回来和他见见面咯……”
电话什么时候挂了也不知道,我失魂落魄地靠着桌沿站着,脑海里回荡着大伯娘那干涸沙哑的声音,还有那加重了语气的六位数。
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室友不满的声音又响起在耳边时,我才回过神来。但这次来不及安抚室友的情绪,我连忙拨通爸爸的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转打妈妈的电话,也是一样的情况。
最后目光落在桌面上的台历,显示着还有两天的时间,就是这次的清明放假日了。家里距离远,如果要回去,现在就要请假买火车票连夜回去。
我用力捏着手机,直到指尖逐渐泛白,不注意咬了口下嘴唇,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给辅导员打电话,语气恳切惊慌,结结巴巴地请假,得到同意后,连忙收拾东西去赶回老家的车。
在车上,一直混乱的思绪这时候才慢慢静下来,但一股不安的情绪渐渐弥漫上我的心头。车上信号不好,拨出去的电话铃声时断时续,一直没有等到人接听。
我心里一边担忧妈妈的病情是不是又恶化了,爸爸还有没有钱交医疗费,一边给自己做心理暗示。
我,你要坚强,如果那个人是好的,你就答应了吧,妈妈需要这笔钱做手术,你可以的,爸爸妈妈需要你。
回程的路上遥远,除了大伯娘偶尔打来的电话问路上情况,催促我赶紧回去,期间一直没有收到爸爸妈妈的电话。
我很担心,却没有办法,只能把要说的话全都编辑成文字,发到他们的社交账号上,期待他们在空闲时能够看一眼,给个答复,让自己安心。
我从大城市转进小县城,坐完火车坐大巴车,整个人又饿又困,车上有人推着推车售卖东西。
我没有钱,只是看了几眼,而后紧紧抱着怀里的书包,偶尔不出声的催眠自己入睡。
在大巴车转进镇口的路上,我恍惚间听到了一种念经的声音,整个人听得昏昏沉沉,又像是一阵大风吹过,整个人无意识地飘了起来。
接着就听到了大巴车“砰”的一声,整辆车似乎是要翻滚起来,我完全动不了,耳边是所有人员惊慌失措的声音,以及最后响彻车厢的怒吼:
“敲!司机你会不会开车?”
2.
我睁开眼的时候,看着眼前的场景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像是回到了老家小时候一直住的房间,一窗一户的格局都没有什么变化,夕阳透过窗户洒落在室内,室内的装饰和布景却格外不同,全是白色与大红色交织。
不等我有什么反应,一直站立在窗边的婶娘,立刻朝外挥挥手,接着从门外涌进来四五个人。
她们彼此间没有言语,只凭着眼神交汇,动作利落,将我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剥下,又给套上了以暗红色为主色的长服,像是古代人穿的新娘嫁妆。
我只觉得全身酸软疼痛,整个人能动的地方只有一双眼睛,此刻由于整个人没有清醒过来,两眼看东西都是雾蒙蒙的。
我口渴想喝水,嘴唇刚微微蠕动,被一个婶娘发现了,一张带着厚茧的大手迅速糊了过来,将我没出口的话摁了回去,并轻轻摇了头。
另外的婶娘给我编头发上妆,穿红鞋,最后一块红布从头上滑落,遮住了视线。一个婶娘蹲下,其他人将我放在了她的背上趴着。
窗外唢呐的呜咽声在一片寂静中响起,凄切的语调,声音悲凉,天边的落日还有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却平白给这间屋子渲染了鬼泣森森。
我的身体随着婶娘的走动颠簸着,思绪仿佛被扯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深渊里,格外粘稠。
我并不知道,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童男童女们端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往回穿梭,所有人都是脚步轻轻,彼此间碰到了也不对话。
在进入堂屋的时候,我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想要起来,背着的人感觉到了,轻轻往我的臀部拍了拍,像是在安抚又像是在警告。
红布遮挡了视线,我看不见周围,透过烛光,只模模糊糊地看到眼前晃动的人影。我太久没有回过老家了,除了坐在主位的大伯娘,站立在一旁的大堂姐,其他人都没有印象。
我趴在背上,身体跟着婶娘的跪趴站立而起伏,周围有人帮忙扶着,迷迷糊糊听到“礼成”的那一刻,感觉周围所有人的身体好像都松懈了一些。
我却昏了过去,昏倒那一刻,身体不自然颤抖了一下,仿佛被吸走了一部分灵魂,发着七彩的光泽消失在空气中。
而周围的人还在木然地按着流程做其他事,一步一步地,将她送进了一个燃着香的房间里。
3.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这次屋内没有其他人在。
两眼放空地看着天花板许久,最后头晕脑胀地用手撑着自己坐起来,一个男人从门外走进来,脚步一踏一踏地,像是拖着沙子走路般沉重,把我的思绪引了过去。
我眼神迷惑地看着他,那男人目光复杂地回看过来。我不认识他,潜意识在告诉我这是我结婚的对象。我俩无声对视了一会后,男人将手里捧着的一碗灰褐色汤水递来,语调嘶哑地说道:
“这是妈给你做的汤,你喝了吧。”
我双手捧着接过,略带犹豫地看着,在男人无声的催促中,感到了强烈的压迫感,只能匆匆的几大口喝下。
汤很难喝,像是煮糊了材料都被煮糊了,还有草木灰放进去一起煮着的感觉。
我喝完就想吐,但是男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仿佛我只要敢吐出来一口,就再捧一碗进来给她喝,喝到不吐为止。
我只能强行忍住吐意,将涌上喉头的汁水悉数压下去。
男人大概是看我想吐也吐不出来了,这才僵硬地扯出了一抹笑容,满意地将碗接过,拖着身体一步一步朝外面走去。
又是躺了很久,感觉恢复了行动能力的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走出房外。
这个卧室给她的压力太沉重了,待在里面像是无时无刻都被什么东西吸着,思绪混沌。
我找了块干净的墙面倚靠着,这里所有的事物都很熟悉,像是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这里,却又透露着一种陌生的违和感,来往路过的人见着她总要说一声:“新婚快乐!”
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快乐,但只能强装着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回应,一旦不笑,那人板起脸的时候,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压得她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