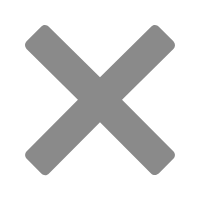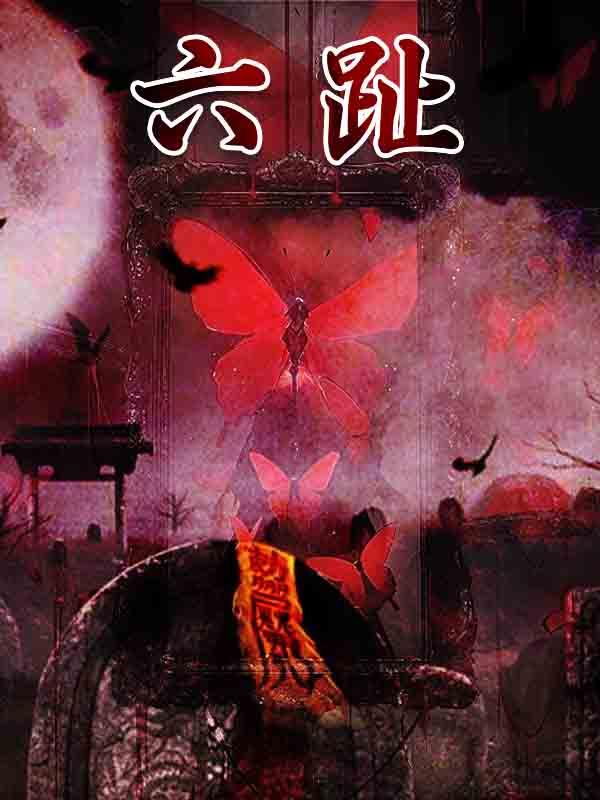
-
六趾
1
我四岁的时候,吃了满满一碗的头发。
这头发是我弟的,他天生六趾。
神婆给我妈说,这是我在娘胎里作的恶。
1
「生了!生了!是个小子」
夜半,只听屋内那孩子嗓音嘹亮,亢奋万分。
我在灶沿前蹲着,用石子划拉身前的地,困得不行,画出来的线都是歪歪扭扭,难以入目。
「啪!」
我爸一巴掌打在我的头上。
「水都烧开了不给你弟拿过去,等着烧干吗!」
本来就十分混困,这一掌挨得脑子更加反应不过来,直愣着哭。
「哎哟,丫子,这可不兴哭,这可不能哭啊」
神婆见我满目泪光,连忙摆手,说此时我弟刚生出来,很是脆弱,我这一哭,会把霉气带来。
「狗屎蛋子,一天天净不干好事!」
我爸一脚给我踹来,我人连着手中的开水一起倒了下去。
我倒在地上,开水倒在我的身上,泼在我的眼角,留下了好几处烫伤疤。
「这,这是个六趾娃!」
稳娘慌张的跑出来,一时间不知道该对着我爸还是神婆求救。
「六趾?怎么会是六趾?不可能!我老陈家绝不会有这种!」
我爸先是惊恐,疑惑,再到自信的认为,这不是基因所致,一定另有缘故。
「完了!完了!应是这丫子在娘胎里做的恶」
神婆指着我,眼神恶狠狠的。
说是我在娘胎的时候干了坏事,把那些坏果留在我娘肚子里,被我弟吸收了去。
一时间院里的人都用那种眼光看着我,嫌弃,憎恶。
「我没有!我没有做坏事!」
我委屈,从地上爬起来就往神婆那撞,我讨厌死这个胡说八道的老太婆了。
「天爷哟,你看,孽障,这真是个小孽障」
神婆在我们村里威望很高,死去的人要经她处理,生来的娃要经她验看。
大家都说,她是能通神灵的人,不可冒犯。
我这一撞,把大家都吓坏了,我爸更是害怕,顺手拿起刚刚和我一起摔在地上的烧水壶就向我砸来。
「爸爸,我才四岁啊」
我爸还没看见我手上比出的四,就被神婆拉到了里屋。
「你丫子,四岁?」
「怪不得,怪不得你小子六趾!四通死,不吉利。她在娘胎里做的恶,今年怕是最煞之时,全给你小子吸收了去,怕是难活。」
「那怎么办?神婆,你救救我小子吧,我就这一个儿啊」
「这,要将你小子的毛发全脱了,伴着香灰让你丫子吃了去。」
「这恶气,随着你小子的毛发长出来,是你丫子做的恶,就必须要让她收了去,不然断不了根,恶气还是留在你小子身里。」
「还有,每年的今天,往瓶子里装120块钱,趁黑夜没人的时候,放在你家门口,给天神送去,才能得它庇佑。」
「爸,我不吃,我不吃!」
我爸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里面是我弟的头发,混着香灰。
「谁让你把你弟害成那样的?这是你欠他的,就得还!」
我很害怕,真的,一下闯入我妈的那间屋子,扑通跪在她面前。
「妈妈,我怕」
刚生产完的她满脸憔悴,却还是使出精力对旁边哭喊的弟弟说是妈妈呀,别怕。
她没应我,我就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角,她撇过头来,像是连一点说话力气都没有了一样的看着我,竟是跟刚刚那群人一样的眼神,嫌弃,憎恶。
「妈妈,吃了这个,我会死吗?」
2
不会的。
我用亲身经历证明,吃下满满一碗头发,是不会死的。
只是干呕,只是总有头发卡在嗓子眼,上不来也下不去的难受感。
自我弟出生以后,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以前是不用的,以前我爸妈只把我背在背篼里,把我放在田坎上。
我就拿个拨浪鼓在手里玩,等他们干完活再一起回家。
有时会遇见叫卖的,卖豆沙小馒头,五毛钱一袋。
我爸每次都会买上一袋,把外面的白面掰给我妈,里面的豆沙馅留给我,甜的,我爱吃。
不过从吃完头发那天起,我就再没吃过豆沙小馒头了。
接下来,就只有给我弟洗尿片,给家里喂猪,烧火,拖地。
再大一点,就要砍柴,砍猪草,做饭,给田里的爸妈送去。
「老陈,你家珍珠必须得去上学了」
「女娃上啥学,反正也是要嫁人的」
「可不行,现在时兴九年义务教育,不让娃上学是要犯法的」
「行行行,知道了」
偷听到我爸和村长的对话,我开心得把饭放下就往回跑。
跑到东头卖烧饼的铺子,又往西,跑去西边最大的那个塘子。
「耶!我要上学啦!我要去上学啦!」
我的脚在塘子里打出水花,我冲着里面惊慌的鱼开心的大喊。
「哪有钱上!」
我哼着小调,还没走到家就听到了我娘的声音,正给我爸细算家里的钱呢。
「家里就这些,这,是买种的钱」
「这不能动!一家人全靠这生计」
「那,这是买粮食的」
「这也不行,上个学一家人跟着喝西北风」
「还剩181,120块要给天神送去,这六十几块钱,万一娃有点事...」
听我娘这么说,内心的光暗淡了下来,狠狠的掐着自己,不让自己哭出声。
「学费要多少?」
我爸又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听起来他还是想让我上学的。
「村长说120块」
「那是不够」
「那怎么办!不去,是要坐牢的!」
我妈冲着我爸喊叫,她说神婆说的果然没错,我真是个孽障,净给家里坏事。
「如果,如果她丢了呢?」
3
当晚,我爸妈就把我关在柴房里。
还没睡醒,就听见我妈在院门口哭。
「我们家珍珠丢了,她爸找了一夜也没找到」
「这可怎么办哟,我们家珍珠才多大点人」
「陈家媳妇,我昨天看见她往西边跑呢」
「哪有!我看见是往东去的」
「不对,是在西边,我昨天还看她在塘子那玩呢」
门口来了一堆人闹闹呼呼的,都吵着说在哪哪哪瞧见我了。
「妈妈,我在这,我在这!」
我正想站起来,才发现我早已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
嘴也粘上胶条,叫不出声。
「哈哈哈!你真的好像一头猪」
我正挣扎的时候,弟弟打开柴房的门,站在我面前。
「老弟,快给姐解开...」
我粘着胶条支支吾吾的还没说完,这小子裤子一脱就指着我嘴尿。
「哈哈哈哈哈哈,好玩,好玩」
「天杀的!这才是个坏种!」
我暗自发誓,将来有机会,一定要给他剁了。
「嘶--」
我妈演完戏了,见着柴房里被尿湿的柴问也没问就一鞭子给我抽过来。
「小畜生,住在这就真变畜生了啊!」
「柴湿了怎么用!」
她不解气,又狠狠抽了几鞭。
「不是我,是弟弟」
我委屈的看向她,以为能得到一丝怜悯。
「不学点好!小小年纪,骗人,还诬陷到你弟头上」
她手中停下的鞭子又挥了起来,呵,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早知道,我就不来这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