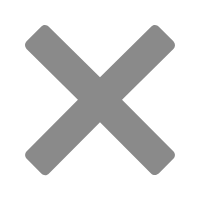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
婴
1
我和老公去看望生病的婆婆。
对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病友,刚进门就一直盯着我,神色古怪。
我把水果放桌子上时,她终于忍不住问。
“姑娘,你咋后面还背个都是血的娃娃啊。”
酷暑七月,我和老公面面相觑,惊出一身冷汗。
1
我是一名法医,坚定的无神论者,平时就是接触尸体解剖。
不过这个行业,在老一辈人眼里是不适合女性的。
比如我多年不孕,我婆婆一直认为是行业晦气,阴气太重,恨不得让我立刻辞职当家庭主妇,给她生个大胖孙子。
我嗤之以鼻。
我和我的老公岳峰云大学认识,那时候我还被冠为xx届的清冷系花,他追我到毕业后才同意。
我也并非对他无意,只是很享受被人追捧的感觉。
更何况如果不是这段爱情对他说来之不易,又怎么会对我一直珍重,视我为唯一。
结婚之前他接受了可能不会要小孩的提议,我嫁给的是他,又不是他的婆婆。
这件事灵异的开始,大概要从最近解剖的一个新生儿说起。
那是才生出来的小孩,瘦瘦小小的没几斤,一只手就能托起来。
小孩子的肺和成人不一样,没有经过太多尘埃,鲜嫩润红。
我把它放进水里,看它沉入器皿底,晕开飘飘缕缕的血,混成一腔绯色,又慢慢悬浮上来,沉默诉说我们想要探寻的真相。
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
接生的医生资质已老,明明都拍了好几下新生儿背,还是听不见啼哭声。
婴儿血淋淋,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地伏在他手上,他叹口气说,是个死胎。
没有抢救,事情就那么处理了。
可是隔天就因家属不满其诊断告入法庭。
原告哭天抢地,哀恸有余,说他们的孩子十月怀胎啊,怎么会死呢。
各执一词,无根无据。
根据就到了这里,受害人本身。
“所以这次我们鉴别死亡时间的证据,是肺。”我脱掉橡胶手套对新人解释,“浮起来就是有空气,沉下去就是没有在外界呼吸过。”
胎儿一直在母亲羊水中,直到出世的第一声啼哭,告诉这个世界他来了,同时吸进第一口从今以后都赖以生存的氧气入肺。
可是谁又规定数以万计的新生儿都要以这种啼哭的方式到来呢?我颇为可惜看了眼这个才出生就结束的小生命。
没有任何征兆,它转过脑袋来,皱巴巴的黑红脸上眼睛猛地睁大,古怪的黑色没有一点光泽,没有眼白的眼球空洞骇人,咧开嘴像是在笑。
“妈妈……”
我呼吸一窒,指甲已经深深嵌进肉里,心跳急速跳着,掌心的持续的痛意跟我说这不是在做梦。
什么鬼,乱叫什么妈妈,是幻觉吗?
是幻觉吧?
我眨了眨眼,果然如约消失,上面还是安安静静躺着开膛的尸体。
2
“阿良。”我叫旁边那个身形高大的年轻人,嗓子有点发紧,声音也带着微不可闻的颤抖。
“你刚刚···有看见什么吗?”
“啊?没什么啊。”阿良莫名其妙摇摇头,看向死婴,接着开起了玩笑,“总不可能梁姐也学别人开玩笑,要说这尸体动了吧?”
我也顺着笑了笑,没接话。
后面倒是再也没有这种幻觉了,只能归咎于那天太晚,前几天又看了场最近算比较热的鬼婴题材片子。
鬼神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子不语怪力乱神,根本也只是要让自己端正己身而已。
我在职这么些年,平心而论尊重死者已经成了我比孝敬父母还排位前的事,问心无愧。
揣着这种想法,过了一阵好长的日子,也没有别的异象。
可是这没有异象的日子里,我又忍不住乱想,想到我最不愿意提起的往事。
3
我向峰云提出丁克的想法。
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小孩,害怕生产开十指的剧痛,各种产后问题,是因为我,很难生育。
这件事情岳峰云知道。
欲望太重,而才华不相匹配,偏还有张脸,我那时居然还觉得,这是老天赏给我的。
我也看不上学校里那些青涩的,伸手向父母要钱的男生,一次碰巧,我认识了我大学的金主。
金主年龄大概和我爸差不多,不过我父亲常年劳作,比他又不知道显老多少。
我主动接近他,装着清纯可怜的模样,成功地下药勾引他上了床。
礼义廉耻,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害怕被发现会被成堆的人怎样说道。
小狐狸精!
臭婊子!
小三!
我攥着那张里面的钱比我一年学费还多的卡,一点喜悦也被没有出现的舆论逼得烟消云散。
不安稳,以后不要了,我想。
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才做一次,后悔一点也不晚。我安慰自己。
我受不住啊,这些的东西。
受不住是我想的,可是踏出一步想缩脚却被拽住了,狠狠拖进了泥沼。
他食髓知味,隔了很久之后居然还找到我,很愧疚地带我去吃啊,玩啊,买啊。
高档的东西把我衬托得又土又穷,他的温柔体贴还和水一样无孔不入,他来吻我。
我匆忙推开他,他就和我说酒店那有摄像头,找到了他头上,他也要找我头上。
语气还是温温柔柔,好像说话的内容就是说明天天气还是很好一样。
他有钱能摆平,鬼知道他老婆知不知道,知道了会离婚会闹还是闭一只眼忍了。
可是我呢,我能拿什么东西摆平,我家里人知道我会怎么样,被同学学校知道了我能怎么样。
那时候我才知道,女人光有姿色不够,我的小聪明也不够,我怕得太多畏畏缩缩,走不了那条又偏又险的捞钱路。
我就像是丧失人权的奴隶,他后来弄得越来越变态,下面伤到了,衣服底下淤青几天不消,正常活动都会扯痛皮肉,我还要笑着装乖去讨好他。
我见识浅,看不懂哪些是酒肉饭囊玩女人的,哪些是真阴狠来玩人的。
他拽着我头发仔细端详我这张脸,雾状的白吐在我脸上,呛得我眼里都是泪。
“下三滥的手段就算了,我看你是处也不亏待你,怎么还让我老婆知道了,闹得我们家不愉快呢。”
他把话挑明了,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的笑话,我拿着钱活该我受着怕担着苦。
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不信鬼神,我信因果报应,却不信有菩萨度人出苦海,都没有菩萨了,凭什么还有恶鬼。
不过万幸,那个带玉扳指的有钱人怎么也没让我身败名裂,大概大二后他也没找过我,可能是因为生意忙没工夫管我这种小杂鱼,就那么慢慢淡出我的世界。
创伤却是永久的。
精神上的,还有身体上的。
我拿着钱好好打扮自己,一股脑发狠地学,拿奖学金,进学生会,总有人追求我,他们看到我漂亮矜持的模样,不知道我有多烂。
我有过他的孩子,他知道我的专业,本以为我懂这些,不会要我们两个都麻烦的。
可是后来我演着老套的借子相逼,自然是上不了位,却让我少受了很多毒打,还有一笔打胎费。
那时候医疗技术不是很好,医生说我以后可能很难怀上了。
这是唯一我做错的地方了。
打胎的时候才四个月,那么小的东西,过去了六年,还要找上我?
那那个混蛋做了那些事怎么不找他啊!
我窝在房间双人床的角落里,再次被灰色的回忆伤得蜷缩闷哭,更何况还强加了一点来自未知事件的恐惧。
4
老公出差回来,还没有洗去一身风尘和疲惫,到家就搂着我黏糊。
我那时候正在厨房给他煲汤,敏感的后脖子被亲来亲去,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叫他去外面等,心里甜甜蜜蜜。
都说小别胜新婚,这只大型犬一样的男人完美阐释了这句话。
当晚顺理成章给他加了个宵夜,柜子里的套用没了,我被撩拨得难耐叫他直接进来。
我对这方面的欲望一直比较高,尤其是这种心慌不安的时候。
完事后,我窝在他怀里昏昏欲睡,他逗我鼻尖提起小区里发春的猫。
“楼下的猫真可怜,发情了没人管,我就不一样了,我有漂亮老婆疼。”
这种油腻的话换一个人说我都会受不了,得亏峰云长的不算寒碜。
“叫了好几天了,撕心裂肺的听了难受,还个娃娃音。”
猫是个奇怪的动物,大眼短鼻就很符合人类婴儿了,它发情的声音还像。
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