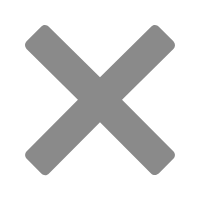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
庄生晓梦
庄生晓梦
我是定北侯府上最不起眼的侍女。
众人皆道定北小侯爷心志坚定,不好女色。
却无人看到,芙蓉帐中,谢观尘和我紧紧交握的手。
后来,谢观尘不顾世人反对,坚决迎我为妇。
独处温存时,我将匕首狠狠捅进他心头。
音色淡淡,
“谢观尘,你终于能去死了。”
1.
我叫昭兰,是定北侯府上的洒扫婢女。
换做从前,这个时辰,我应该蹲在后院,搓洗主子们的衣裳。
但今夜不同。
我紧紧攀附着面前少年的肩膀,又急又难耐地舒了口气,
“小侯爷……”
衣裳被褪到腰间,谢观尘纤薄的唇瓣贴着我的耳垂。
他半闭着眼睛,俊脸红艳,水光盈盈。
指尖摩挲着我的肌肤,带起一阵酥痒。
少年近乎恳求般道,
“昭兰姐姐,你别动,我碰碰就好。”
我忍不住颤栗,嘤咛出声。
夜凉如水,万籁俱寂。
婢女和公子,多像画本里说的那样。
半个时辰前,我奉了嬷嬷的令,来给谢观尘送宵夜。
一碗甜汤,京中贵人爱喝的那款。
往日从来没出过事,今夜却不知怎的,谢观尘喝完之后,突然兽性大发。
向来淡漠的小侯爷,一下扯开了我的衣裳,
只是唇舌交缠,便让人无法招架。
墙上挂着谢氏家训,端庄持重,忠君报国。
而我,就被谢观尘抵在这块牌匾旁。
就像谢家先祖在旁观看,此等糜乱情景。
别样的,刺激。
腿根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触感。
我眼眸低垂,软声道,
“小侯爷,奴婢害怕。”
谢观尘显然没有耐心。
他象征性地抚了抚我的脸颊,哑着嗓子呢喃,
“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
我沁出几滴眼泪,小声嗯了一声。
夜深了。
打更人从窗外走过。
却未看到,摇晃不止的芙蓉帐慢。
2.
翌日醒来,已是日上三竿。
谢观尘早已走了,身侧不留一丝余温。
床边矮桌上,放着一碗苦黑微冷的汤药。
不用说我都知道,是避子汤。
我闭气,一股脑地灌下肚子。
穿好衣裳,若无其事,继续做工去了。
相熟的小婢女见了我,惊讶感叹,
“昭兰姐姐,你今日好不同,就像,像……”
她绞尽脑汁,憋出一个,
“一株,刚浇完水的花儿。”
我笑了笑,随意回应了几句。
谢观尘来了。
他大概是刚练完武,衣裳紧紧贴着身躯,显出漂亮的肌肉。
一张俊脸沾着些汗珠,神情却是冷漠的,教人不敢接近。
但京城中,仍有无数名门小姐,爱惨了这朵高岭之花。
我啧了啧,感叹一番,随后迎上前去,福身请安。
“随我来。”
谢观尘惜字如金。
我同他来到书房。
谢观尘紧紧掩住门,抿着唇,有些纠结地盯着我。
又脸红了。
我奇怪道,
“小侯爷有何吩咐?”
谢观尘犹豫片刻,方道,
“我原以为,过了昨夜,便不会再有那种奇怪感觉。”
“但方才练武时,我,我又……”
我瞪大眼睛,忍不住向下瞥了一眼。
谢观尘慌张地呵斥我,
“别乱看!”
我不动了,乖乖待在他怀里。
谢观尘呼吸有些重,看起来很不自在。
他又纠结了一会儿,才低低开口,
“可此物很怪,只有想到你时,才能平复些许……”
我了然地哦了一声。
主动解了外衣,从善如流道,
“奴婢愿为小侯爷分忧。”
一片雪腻酥香。
谢观尘呆呆地看着我。
脸庞红得快滴血。
“你,你不怪我……”
“您是定北侯嫡子,京中顶顶尊贵之人,奴婢何敢怪罪您?”
“况且,奴婢十岁来京,承蒙侯爷夫人收留,谢氏一门,对奴婢有天大的恩情。”
“侍奉小侯爷,是奴婢的分内之责。”
我柔声劝慰,言语间滴水不漏。
谢观尘更动容了。
即便自己忍得再艰辛,也不再像昨夜那般,强取豪夺。
书房案几上的笔墨散落一地。
余韵散去,谢观尘拥着我倒在一起。
他拨开几缕黏在我额角的发丝,音色低且温柔,
“今日起不必再在偏房洒扫,做我贴身侍女吧。”
“花朝节过后,我会替你向母亲求个名分。”
闻言,我露出感恩戴德的神情。
“多谢小侯爷。”
谢观尘吻了吻我的额头。
十分靥足。
3.
我走出书房的时候,刚好撞上了定北侯夫人。
乔氏年过四十,却因保养得当,肌肤平滑如少女。
眉宇间,亦还留存着颇多当年随定北侯征战沙场时的狠辣果决。
“见到夫人,还不跪下!”
她身旁的侍女率先开口。
我暗叫不妙。
随即有人上前,不由分说摁住我肩膀,生生把我摁得跪了下去。
膝盖传来酸麻的痛感,我忍住痛呼,乖乖给乔氏叩头,
“夫人息怒。”
乔氏高高在上,满眼冷淡地俯视我。
却藏不住刻在骨子里的轻蔑。
“花朝节将近,郎中曾嘱咐我不得动怒,奈何府中风气不正,我儿身边,竟存有心思放荡的腌臜之女。”
“夫人明察,奴婢万不敢有引诱小侯爷之心。”
我当即辩白。
乔氏讥笑,
“你先别急着狡辩。”
“我记得,你无父无母,流浪至此,可对否?”
我不明所以,乔氏继续道,
“我儿偏宠哪个奴才,我是无异议的。”
“正巧,侯爷近日身子不适,若此时,府中诞下新子……”
“这会是多泼天的富贵,你自己掂量。”
她嘴角微勾,暗示地对我笑了笑。
名门之女,短短几句,便已挑明了己欲所求。
其实不止帝王后宫有相争,寻常的贵族后宅,儿女之斗、妻妾之斗亦层出不穷。
定北侯年事已高,却仍未将爵位正儿八经地传给谢观尘。
乔氏虽为发妻,但并未真正掌权,后院十三房姨娘,个个如狼似虎。
而且前日,定北侯又迎了一房妾室进门。
乔氏着急,是意料之中。
我已看得分明。
我当即颔首,
“昭兰愿为夫人效犬马之劳。”
乔氏满意地笑了笑,朝她侍女努了努嘴,
“确是个聪慧姑娘。”
“这三两黄金镯,算我送你的定金。”
“事成之后,本夫人,要去母留子。”
她特意加重了最后四个字。
我心中一凉。
轻轻答了声是。
4.
我悄悄住进了谢观尘的庭院。
专门伺候谢观尘的起居。
谢小侯爷其人,年少成名,天生将才。
丰神俊朗,热情亦十足。
谢观尘带着我享了半月欢快日子。
他停了避子汤,美其名曰怕我伤了身子。
花朝节前日,谢观尘终于消停下来。
据说是乔氏为他相中了一位名门贵女,要他好好准备着见那位小姐。
侍女们偷偷传言,这次这位,基本上就是定北小侯爷既定的夫人了。
我倒是无所谓,谢观尘却不知怎的,原本一整天都好好的,日头一落,忽地又开始发病。
“昭兰姐姐,你可在意我?”
“你,你可会因我感到些难过?”
谢观尘埋在我颈窝里,闷闷地逼问我。
我攀着他脊背,轻声道,
“奴婢不敢。”
谢观尘沉默片刻,忽地低笑一声。
指腹擦过我的唇珠,像是又欢喜起来,
“不是不是,而是不敢。”
“昭兰姐姐心中有我。”
我一时有些出神。
他拥着我,挤在窗前,薄薄的唇瓣衔着我耳垂轻摩。
“昭兰姐姐,卿卿……”
“我,我好心悦你……”
我嘤咛着仰高了头。
谢观尘又吻上来,脖颈处一片酥麻。
结束之后,谢观尘命人端来水和帕子,亲手替我擦身。
“小侯爷和昭兰姐姐感情真好。”
小侍女艳羡感叹。
谢观尘神色淡漠,
“看到不该看的该怎么做,要本侯教你吗。”
小侍女一愣,随即惶恐地跪下。
谢观尘轻哼一声,道了句滚。
我躲在帷帐后,目睹了这一切。
忍不住感慨,这才是我记忆里的谢观尘。
我刚入定北侯府时,就听资历老一些的嬷嬷讲,小侯爷天生性冷,六岁上沙场,手段是非常人的狠辣。
他对待府中侍从,亦不会轻易给了好脸色。
我初见他那天,不慎打翻了一盏茶。
彼时谢观尘还是个俊秀的小少年,看我的一双眼,却满是在上位者的冷峻轻嘲。
他罚我举着烧得通红的瓷壶,在冰面上跪了整整一夜。
我的手被烫得开裂,半月不见好,还因做活慢,被嬷嬷减了三月月俸。
那时候,谢观尘不知道我的名字,也没记住我的脸。
他自然也不知,随意一句话,就会极大改换旁人命运。
这几日,我有时候会想,若没有那夜的甜汤,我在谢观尘眼中,依然是个记不得名号的奴婢。
人们都说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可实际上,种种虚化富贵,不是我的,终不是我的。
我心头冷了下来。
谢观尘似是察觉到我情绪变化,关切地凑过来,
“卿卿,你还好吧,可是累着了?”
我看着他俊丽的眉眼,轻轻摇头,
“奴婢只是想到,自己身份卑微,和小侯爷云泥之别,即便来日,能有幸侍奉在您身侧,可……”
“当家主母,妾室姨娘,又怎会给奴婢好日子过。”
我适时落泪,抽噎嘤咛,梨花带雨。
谢观尘神色心疼,将我搂在怀中。
“原来在担心这个。”
他抬手,替我拭去眼尾的泪滴。
像是承诺,
“只要我在定北侯府一日,就绝不会置卿卿于孤苦伶仃。”
我感动地答了声好。
唉。
单纯的小傻子。
5.
花朝节是上京贵族之间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城无宵禁,专门留给小姐们观湖赏花,同自己心悦的公子互送信物。
平民百姓们,也能守在道路两侧,得一些贵夫人的赏赐,
过去几年,我们这群奴婢,只有给夫人姨娘看马车的份儿。
今日却不同了,谢观尘特准我和他一起进了内城。
他一直牵着我的手,不时来一句,
“卿卿,这朵纱花你可喜欢?”
“这糖人儿做得也好看,我一齐买给你可好?”
“你不是说喜欢素缎子裁的衣裳,我看这件就不错……”
乔氏走在我们身后,不咸不淡地开口,
“尘儿倒是心爱此女。”
我脚步一滞,谢观尘率先开口,
“还要多谢母亲将昭兰赐我,我二人情感甚笃,感念母亲大恩。”
乔氏冷笑,
“好一个情感甚笃。”
下一秒,侍女上前,重重分开了我的手。
谢观尘拧眉,上前想将我拉回来,乔氏又道,
“丞相家小姐已在画舫里候你多时,你若不去,该教丞相如何看我们定北侯府?”
谢观尘面露不悦,似还想和乔氏争辩。
乔氏朝我递了一个眼神。
我会意,开口劝慰,
“小侯爷莫动怒,夫人说的在理。”
“丞相府总是怠慢不得的。”
谢观尘怔了怔,眉宇间萦上些委屈。
我看了看乔氏,又压低了些声音,
“起码要做些表面功夫,小侯爷不喜,回来大可同奴婢讲,奴婢不想看您和夫人生了罅隙。”
谢观尘这才作罢。
他走了后,乔氏冷哼一声,
“狐媚手段,果真下作。”
“这才几日,就把男人迷得丢了三魂七魄。”
我心知此刻绝不能顶撞乔氏,便蓄了满眼泪水,柔声求情,
“夫人息怒,是奴婢擅作主张,弄错了您的命令。”
“您罚我吧,莫要迁怒小侯爷。”
乔氏讥笑,
“你多虑了,我岂会迁怒我儿?”
她顿了顿,眼底多了些不屑,
“把他迁走,无外乎,为的是提醒你。”
“一介女奴,休要肖想不属于你之物,可懂否?”
我低眉敛目,软软说了声是。
乔氏轻哼一声,挥手,让侍女松开了我。
她像是嫌脏般,掏出帕子擦了擦指尖,
“滚吧,今夜我儿大事,休去他眼前放浪。”
此地人去楼空。
我倒在地上,浑身发冷。
钻心刺骨的痛意像蚂蚁般侵咬着我的血肉。
每年的花朝节,都是我犯病的日子。
那是我出生便携带来的顽疾。
只是从前在草原上,有母妃和父王为我熬制药汤。
但现在,没有了。
我忍不住落泪。
再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