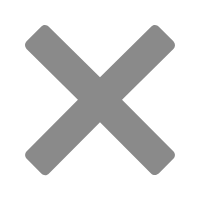-
求不得
1
五年前,我娶了年少时最爱的女孩。
我以为我的人生会就此圆满。
可这五年里,许颂宁愿做别人的便宜妈妈,也不愿意看看我和她的女儿。
直到两天前,我女儿意外身亡,她都在陪着温询的女儿。
1.
我的晚晚死了。
而我对许颂的爱意,也随着晚晚的死消失s殆尽。
我看着她小小的身躯毫无生气地躺在棺材里,周围是她最爱的小苍兰,只觉得我最后一点念想都没了。
我看着通话记录里拨出去十几通却没有接通的电话,终于放弃了。
“许颂还是没有接电话吗?”
一声苍老而又有些疲惫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我将手机放回兜里,转身就见到那个不知道何时头发又白了不少的许父。
从我爸爸为了救他而丢了一条命,他为了替我爸照顾我们孤儿寡母,把我和妈妈接进许家,让我妈做了许颂的钢琴教师起,许父在我记忆里从未这么疲惫而又脆弱过。
我摇摇头,走向晚晚的棺材旁:“她可能在忙,更何况……”
更何况,许颂本就厌我,她认为这场婚姻是我和我妈算计得来的,所以她也厌恶这个被算计得来的女儿。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伸出手来替晚晚整理她的头发,我的晚晚最爱漂亮了。
许父敲了敲手里的拐棍,看着像是熟睡了的晚晚,突然老泪纵横:“她是晚晚的妈妈,真是胡闹!”
我没说话,只是向前来的宾客鞠了躬,我知道,她可能在陪着温询和温柠在芬兰滑雪。
我刚起身,外面突然传来保姆李婶的声音:“小姐,你终于来了,你快去看看晚晚吧。”
再转头,就看到许颂冷着一张脸进来,仔细看额头上还有着细细密密的汗珠,我看了一眼她搭在手上的羽绒服,心下了然。
许父坐在椅子上,铁青着脸看着走到晚晚棺材边的许颂:“你还知道回来!”
许颂罕见地没有顶嘴,只是神色复杂地看着棺材里了无生气的晚晚,她颤抖的伸出手想去触碰晚晚的脸颊,却最终还是收回了手。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希望她看到晚晚的尸体能跟我一样伤心吗?
明明在她的眼里,晚晚甚至不如路边站着的陌生小孩惹人怜爱。
许颂转身走到许父面前:“爸,你去休息吧。”
许父坐在椅子上看了许颂半晌,终于起身拄着拐杖由许颂扶着回了里间的休息室。
也许是站了太久,我的病痛让我实在难忍,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2.
我只能飞快离开我的晚晚回到房间,我刚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胶囊和药片都吃下去,许颂就推门走了进来。
“抱歉,我在飞机上,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许颂走到我的身边,低着头,语气里竟然真的包含了歉意。
“我知道的,你在陪温柠而已。”
我把药瓶放回包里,没有转过头去看许颂,我以为晚晚走了,我就不会再心痛了,但说出这句话,我的心里就好像破了个洞。
“不是,你知道的,我去芬兰是谈合作,陪温柠只是顺便...”许颂神色略带慌乱的的解释着。
不重要了,什么解释都不重要了,晚晚已经没了。
“无所谓了,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我将空了的一板药盒扔进门边的垃圾桶里。
我有点无力,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从前,许颂是出了名的冷脸美人,不爱说话也不爱搭理人,可唯独对我却不是,她会对我笑,对我撒娇。
会在我被人骂是没爹的小孩时,帮我还嘴,会在我得了全年级第一的时候,为我高兴,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急得满头大汗。
我还记得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调侃,说我是许颂的「童养婿」。
许颂没有否认只是红着脸带着笑意地捶打她的好友。
甚至,她会在盛夏的夜里握着我的手,跟我说:“俞礼,我们要永远都在一起。”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的呢?
或许是那天,我被我妈下了药,许颂醒来后对我的眼神便仇视的起来。
她认为一切都是我妈妈的计谋。
而温询也是这个时候出现在许颂身边的,许颂所有对我的温柔和耐心,此刻全都给了温询,我不知道她转变怎么会这么大。
也许,她是厌烦了吧,厌烦了许父对她耳提面命,也厌烦了她必须像许父一样把我们当成她的恩人。
我还记得温询曾经把我堵在楼道里,他说:“俞礼,你识相的话,就该离许颂远一点,许颂现在,是我的「猎物」。”
我也想过把温询的话告诉许颂避免她受到温询的欺骗,可她却一脸恨意地看着我:“温询不是那样的人,俞礼,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和你妈一样。”
我不懂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着许颂那张陌生的脸,只能如她所愿不再出现在她的视线里。
3.
我将散落在桌面上的药瓶塞进包里,原本想出去继续陪晚晚,却被许颂抓住袖子。
“俞礼,晚晚她是怎么没的,她好端端的在家里,怎么会失足掉下去的?”我突然感受到抓着我袖子的那只手开始颤抖,“你为什么,不看好她呢?”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从前她对晚晚不冷不热,如今晚晚死了,她才要良心发现吗?
一时间,我只觉得自己嗓子干得生疼,说出口的话都是沙哑得难听:
“呵,晚晚她洗冷水澡把自己弄到高烧不退只是想要见你一面...算了...”
我想起晚晚在我面前咽气时候的样子,心里痛得喘不过气,我忽然觉得跟许颂解释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迟来的良心,迟来的母爱,晚晚已经要不起了。
我将袖子从许颂的手里拽出来:
“是我的错,是我不该爱你,也不该在阴差阳错下和你结婚,更不应该在你不想要晚晚的时候劝你把她留下来,是我没看好晚晚,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看见许颂的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惊愕,她结巴着:“我不是……”
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吧,但是这番话说出来,我只觉得压在我心头的某些情绪在逐渐散去。
晚晚下葬那天是个阴雨连绵的天气,我和许颂坐在同一辆车上,之间却好像隔着银河。
我的腿上放着晚晚小小的骨灰盒,脑海里全是晚晚从前笑着叫我「爸爸」的样子,压抑了整晚的情绪,终于在低头看到晚晚骨灰盒的那一刹那爆发了。
许颂面容苦涩递给了我一包纸巾:“别哭了,晚晚会不安的。”
我没有接她的纸巾,只是胡乱用袖子擦了眼泪。
我亲手将晚晚的骨灰盒放在那个小小的墓坑里,我替晚晚选了个好地方,视野开阔,晚晚一定喜欢。
看着晚晚的遗像,我在心里祷告,希望她下辈子可以托生在幸福的家庭里,父母慈爱,能感受到母亲全心全意的爱。
而不是像这辈子一样,要靠着伤害自己才能让母亲回头看她一眼。
许颂在晚晚的墓碑前放下了一套芭比娃娃的玩具。
“之前晚晚说,她想要一套芭比娃娃,我跟她约好了,如果钢琴比赛赢了的话,就送给她。”
我只觉得心里闷闷的,我的晚晚,终于在下葬的这天得到了那一丝丝迟到的母爱。
温询从人群里走出来,在晚晚的墓前送上了一束菊花,一束没有任何包装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菊花。
天知道我忍得有多辛苦,才能压下想要把那束菊花连同温询一起扔出去的冲动。
温询眼神里带着哀伤走到我的面前,他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节哀。”
随后他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
“俞礼,你知道吗?你的女儿死得太是时候了。”
我放在两侧的手捏紧了拳头:“温询,你这个混蛋!”
我挥拳就要朝温询的脸上揍,却被许颂拦下:“俞礼!温询只是想来送晚晚最后一程,你为什么要打他!不要在晚晚的面前无理取闹!”
温询拍了拍许颂的肩膀,温柔地劝导她:“俞礼只是伤心过度,你不要怪他。”
我看着许颂眼里的失望和愤怒,又看着站在许颂身后的温询,满脸的得意,我抬起的拳头终于放下。
无论过了多少年,许颂永远只会第一时间站在温询的面前,我真的觉得好累啊。
我只能背过身去,看着晚晚的那张笑脸,心里默默地跟她说:“晚晚,再等等爸爸。”
4.
随后几天,许颂意外的没有跟着温询离开,而是回了许家。
我眼见着许父把许颂叫到了书房,他大概是想兴师问罪吧,换做以前,我会跟着一起进去,然后在许父生气的时候劝下他。
可现在,这是许家的家事,我为什么要插手。
我上了楼,收拾了几件行李,又拿走了晚晚最爱的布偶熊。
我刚走到许父书房的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许父的训斥声。
我敲了门,得到许可才走了进去,我将许父扶着坐下:
“伯父,你身体不好,医生不让你动气。”
许父看着我的样子,听见我重新改口叫他「伯父」,他突然就像卸了气的皮球一般。
“小礼,我知道你和颂颂之间有误会,但是,你能不能留下,我会让颂颂断掉和温询的联系。”
我看着许父涨红了脸,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求我了。
其实很多次,我都想和许颂离婚然后带着晚晚离开,甚至那一次,我和许颂连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
但那封离婚协议书却被许父看见,他大发雷霆,被气进了医院,甚至住进了ICU,我和许颂后怕,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再也没有提过离婚,只能这么彼此折磨着。
许父身体逐渐好起来之后,我再一次动了要和许颂离婚的念头,这一次,离婚协议书还没到许颂的手上就被许父发现。
他差点跪下来求我,就算是看在他的面子上,为了晚晚,也不要和许颂离婚。
在我的心里,许父就像是我的父亲一般,我见不得他这个样子,我无奈,只能答应了许父,再一次留了下来,可我却没想到,这一留,却没能留住晚晚的命。
如果我当时执意要走就好了,也许,晚晚还能在我的身边说说笑笑。
“不用了,伯父,我已经耽误了许颂太久了,现在晚晚没了,所有的一切都该回到原点了。”
我将离婚协议塞在许颂的手里:“你把这个签了,你就自由了。”
又将一个插着花的花瓶放在桌子上:“晚晚走那天,只是想摘一束花送你,但是却烧迷糊从二楼踩空了,这个花你收着吧。”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临走之前跟许颂说这些,大概,是替晚晚不甘心吧。
许颂听完一脸的错愕,她一向冰冷的脸出现了裂痕“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想再看许颂这番模样,转身就想离去。
“等等,你要去哪里!你真要离婚?”许颂抓住了我的手,却被我躲开。
我没有回答,拖着箱子转身离开,走得干脆。
5.
离开许家的第四天,我不仅头晕还开始头疼起来,常常半夜被疼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
我只能出门去医院找医生拿药,但我却没想到能在医院遇到沈虞,她这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竟然真的当起了医生。
我还记得当初沈虞拿着数学题来问我的时候,跟我说,她以后想做一个医生,我当时只觉得她在说笑话,她的家世怎么会让她做医生。
沈虞和许颂家境不相上下,但沈虞却是个开朗的性子。
沈虞是我学生时代为数不多的好友,可我再一次看见她,却只想逃,但她却叫住了我。
“俞礼?!真的是你啊!你生病了吗?”
我将装了药的袋子往身后藏,我不想让她看见我那些靶向药。
“啊,有点感冒,所以过来拿点药,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我不管沈虞在我身后叫喊,只是往前快步走,也许是我的身体真的不太行了,终于还是被沈虞追上。
她抓住我的手看到我的药品,瞬间惊了:“俞礼,你是不是得了肿瘤?。”
我想要甩开沈虞的手,却发现她的手劲比我的大:“没有,我只是感冒了。”
“你们在干嘛?”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撞进我的耳朵里。
我转头却见到了我更不想见到的人。
许颂和温询牵着温柠朝我走过来。
温询见到我笑着跟我打了个招呼:“好巧啊,俞礼,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
“嗯。”我冷淡的回应着,顺便把手从沈虞手里拽了出来。
“对了,听说你们离婚了,我准备重新追颂颂,这还真得谢谢你的成全。”温询虽然笑得人畜无害,在我眼里却是那么刺眼。
许颂!你就那么迫不及待吗?晚晚才走了几天?!
我看向许颂,她满脸闪躲,对着温询:“没这事,别乱说。”
我不想再继续听他们任何的话,只能控制住情绪。
“恭喜啊。”我迫切地需要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你们刚才在干嘛?”许颂没有回答温询的话,只是眼神阴沉地盯着我和沈虞。
我清了清嗓子,将装着药的袋子塞进包里:“没什么,偶遇沈医生,聊了几句而已。”
“许颂,你是俞礼的妻子,你怎么让他一个病人自己来医院开药?”
沈虞的语气有些不满,也许在医生眼里,一个「癌症」病人,没有家属陪同,是很罕见的事情吧。
“你生病了?你生什么病了?”许颂皱着眉头看我,语气里竟然少见地有些焦急。
“你难道不知道,俞礼他有可能得了……”沈虞这下是真的不满了。
“没有,我只是单纯流感了而已,不用大惊小怪。”我打断了沈虞的话。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阻止沈虞,大概,是对许颂失望了吧。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沈医生,今天谢谢你。”
说完我就想逃离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等一下。”许颂抓住了我的手,她皱着眉打量着我,“你是不是瘦了?”
“跟你没关系。”我想要甩开许颂的手,却被她抓得更紧了。
她大概也发现了吧,我不过才离开几天,却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你不是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
“不用了,你管好温询和温柠就好了。”我甩开了许颂的手,逃离了医院。
却没看到身后的许颂,皱着眉头,担忧地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6.
最近的江城阴雨绵绵,癌细胞好像也开始作乱起来,眩晕好像比之前更严重了点,我只能每天都呆在家里,哪里都去不了。
等我再见到沈虞的时候,是江城终于放晴的那天,我拿着垃圾下楼,顺便晒晒太阳。
刚转身就看到沈虞出现在我眼前。
“好巧啊,沈医生。”我朝沈虞摆了摆手,准备离开,“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朋友也住这儿?”
沈虞却皱着眉头朝我走过来:
“其实,肿瘤科的主任是我的导师,我无意间看到了你的病例,也知道了你的住址,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需要手术干预。”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这件事,沈虞插手得太过了,我冷了脸:“你是医生,你比我清楚,我能下手术台的几率是多少,你也比我清楚,即使做了手术,我能活几年?十年?二十年?”
“都不是吧,我能活三年已经是老天眷顾,那我何必去做那个手术?”
“可是,俞礼,你不做的话,你连一年都活不了!”沈虞的声音不自觉放大。
“那又怎么样?”我转过头来看她,“沈虞,你管得有些太宽了,你不是我的主治医生,也不是我的家属,我要什么时候死,是我自己的事。”
说完我就往前走,沈虞却不死心地还要追上来。
也许真的是冤家路窄吧,我看到了许颂走过来的身影,她也看到了我。
我刚想转头走,她就迎了上来,我有些好奇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时候,她不该陪着温询和温柠吗?
“俞礼,你怎么又瘦了些?我很担心你。”许颂看着我身上空荡荡的毛衣,眼神里有些担忧。
“用不着你关心。”我看着许颂的脸差点笑出来,“你不是应该更担心温询和温柠吗?”
“我爸也想知道你的近况...”提到许父,我终于收起了戾气。
她还想开口说什么,沈虞就叫着我的名字追了上来,看到沈虞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身后,许颂冷下了脸:“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坚决想要跟我离婚,原来是有新人了。”
我原本心情就不好,许颂的话让我更加厌烦:“对,你都能和温询破镜重圆,我就不能?”
“俞礼,你就这么喜欢吃软饭吗!”许颂的音量陡然升高,沈虞想要开口反驳她,却被我抢先一步。
“随你怎么想,你还是去管好你的温询和温柠吧,少来管我了。”
我也不想看许颂和沈虞是什么脸色,转身上了楼。
7.
我将自己摔进了被子里,应付沈虞和许颂,真的让我觉得身心俱疲。
我没想到,原来我一直以来在许颂眼里都是「吃软饭」的形象,也是,当初为了成为许颂的丈夫,甚至开口说可以入赘。
也许在许颂看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为了钱可以连尊严都不要的人吧。
可是她也忘了,当初许家快要破产,是我和许颂两个人将许家一点点扶起来。
我已经数不清自己那段时间在饭局上到底喝了多少酒,以至于许家的危机解除。
我本可以不用管许家的死活,可我妈却拉着我的手说,许家给了我们太多,我就该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许家。
我背负着这些最后却只换来了晚晚的死。
温询给我发了一张他朋友圈的截图。
是一张他和许颂带着温柠在游乐场拍的照片。
温询说:「从今以后,我们仨。」